他是法国戴高乐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全球50余座大型机场的设计者,也设计了巴黎郊外的新凯旋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知名建筑——法国知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于法国当地时间10月11日辞世,享年80岁。据外媒报道,本周一,安德鲁出席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为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举办的晚宴,据到场者回忆,他看起来十分疲惫虚弱。对于工作的状态,崇尚自由的安德鲁此前曾说:“我对建筑结构的轻盈和透明始终抱有兴趣,现在我变得更宽容。其实现在我最大的感觉是,今天的我更自由——我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之中。”
保罗·安德鲁(1938-2018)
安德鲁1938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毕业于巴黎高等工科学院。还是学生时,他对艺术和科学都报以兴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安德鲁写道,“那时的我,刚刚二十岁,正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科学、艺术,这两样都吸引我。对于前者,我知之甚少,对于后者,我一无所知。然而,无知者无畏,哪一样我都不想放弃。为什么不能两者兼得呢?难道就没有两者融合的领域吗?”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完美的结合——建筑领域。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年仅29岁时就设计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从此,作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关西等地的国际机场。2004年,戴高乐机场的一座航站楼倒塌,导致数人死亡。这一事件对安德鲁影响很大,他暂停了自己的工作。
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 Paul Maurer
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 ? Paul Maurer
除了机场之外,安德鲁还设计了英法跨海隧道的法方终点站和拉德芳斯新凯旋门。19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两个世纪以后,这一开创性的项目在巴黎正式问世,成为举世闻名的地标。
安德鲁在国际上也完成过不少负有盛名的项目,他对中国充满热情,曾经设计过国家大剧院、广州新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等。事实上,正是来到中国以后,安德鲁不再设计机场项目,而开始涉足更广泛的建筑类型。“2000年以后,我不再设计机场了。原因是当时我来到了中国,我发现这里有大量的机遇等待着我。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各种大型公共项目。这是让我成为一名独立建筑师的机会。此后,我在巴黎创办了新的事务所,我们有20到25个员工,我们在中国也有建筑师同事。”安德鲁在接受建筑师兼作家Vladimir Belogolovsky的采访时说道。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北京国家大剧院
“我工作的一个动力在于,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是未完成的,等待建筑师用双手去完成它,建筑师通过各种元素,光线、风、水来赋予它生命。我对建筑结构的轻盈和透明始终抱有兴趣。”安德鲁曾这样写道。
除了建筑,安德鲁还会画画,他画抽象画,去年,安德鲁个人绘画作品展“纸间诗语”在北京举行。安德鲁直到晚年才开始绘画,但丰富的人生经历似乎使他对画画有了更多的热情,“像我这样72岁才开始画画,永远比不上15岁学艺的画家,但是我愿意在绘画中传达我50年的目光。”在去年展览期间,安德鲁用纸和丙烯机进行创作,他将纸揉皱,观察它形成的肌理,纹路和褶皱。“我先铺开一张纸,脑海里想这张画可能是黑色的,可能还有点红色,我就开始采用上色,差不多的时候,我在上面叠加一张纸,把这个纸弄湿,下面的颜色会渗透过来,产生一些肌理感,这是事先不会预知的一些东西。这个操作步骤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反而整个过程的无法预料性和惊喜一直发生着。”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Agence Paul Andreu
从设计机场到承接各种项目,安德鲁对于建筑师是否应该“专攻”某一类型的建筑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最好的及建筑是“重新发现某个概念,而不只是对一系列步骤进行打包”,“当我刚开始工作时,那是设计机场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去试验新的想法,因为机场一直在变化和成长之中。”
雅加达机场 Labo ADP
安德鲁的画作
安德鲁读书,念诗,听音乐,画画,这一切都让他充实。不过,在他看来,他的艺术和建筑之间并没有之季节联系,“就像我们的事物和思想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一样。但是一旦你获得了能量,你就能做到一切。”安德鲁不认为灵感和项目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在你的内心深处,必须有一种转化。我很难告诉你哪些想法来自何处,但是绘画无疑是必要的。如果我不画画,我就没有想法。答案在行动当中。在你的大脑、眼睛、思考、绘画和双手之间,似乎有种复杂的联系。”
他曾说:“正是为了绘画,我才去学了建筑,我很乐意和画家交流,我心里觉得绘画这门艺术恰好和科学的贡献是互补的,那时我还从未接触过任何建筑师,这个决定是为了艺术的理想,从此我被建筑所吸引,他占据了我的整个人生。作为起步者和初学者,作为一个年轻的画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像我这样72岁才开始画画,永远比不上15岁学艺的画家,但是我愿意在绘画中传达我50年的目光。”
————
延伸阅读
对话|安德鲁:我处于一种自由之中,望建筑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Q:您对于法国夏尔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的评价?
A:它是我的第一个项目,那时我29岁,却主持设计了可能是法国最大规模的建筑项目。航站楼的统筹、设计,对我来说充满了冒险和挑战。它在1974年后投入使用,在那之后我仍然服务于这一项目长达30年。但我们的确改变了机场的方式,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它是一种超越。
Q:对于中国国家大剧呢?A:最重要的是它所处的场地,它在北京城的中心位置,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它充满了历史、文化,力量…….设计国家大剧院是一份非凡的荣耀,也是一种责任。
Q:听说您设计国家大剧院的灵感,来自一颗非洲的种子。是这样的吗?
A:是的,这东西我一般不给别人看的。它大概是类似面包树种子的东西吧,是我的护身符。像小孩子的玩意儿。每当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我都会把它紧紧握在手里。它能帮我度过难关。其实你可能会发现,我的设计,像一些作家的作品一样,有一个母题,那就是圆形的结构。这不知算不算我的一个情结,可能从精神分析学上能找到答案吧——不过我从来没有请人为自己做过精神分析!
Q:在你的建筑职业生涯中,曾经设计了很多机场、车站、博物馆等,这些项目的目标中最重要的是聚集和组织人流吗?
A:设计机场中重要的的确是如何组织人流。我会尝试去设计人流的循环,让空间去适应这些循环,我的设计从来都不会起始于一个确定的外观形式,组织内在的空间和人才是重要的方面。我们从不设计“盒子”,而是会去观察究竟它的内部会发生什么,而整个的建筑形体则需要将内部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全部包含其中。
Q: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你曾经提出过“扩张”的概念,而公共空间也总是面对着如何开放却又保持独特性,你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有怎样的理解?
A:公共空间必须能够面向大多数人开放,从这一点来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公共空间需要达到一种平均,满足所有的可能,但其实建筑师必须对于人们得不到满足的部分保持小心和警醒。当你在设计公共空间时,你必须注意到人们的需求,而不仅仅只是想推动某件事,或是让自己的名字能够被铭记。你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你需要为什么负责,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需求,甚至人们自己也很难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
Q:你如何看待建筑与城市、人的关系呢?
A:我经常在思考的是,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建筑是有意义的,其实不是结构,有时候我们会思考结构,但是结构并不是建筑,如果拿国家大剧院来举例,设计中如何组织人们,人们的行进路线,我经常会思考这些,当你可以看到充满想象力的剧院,它必须变化,对于我,建筑的责任不是让我自己改变,而是让建筑改变,我希望建筑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Q:您谈及传统跟现代的时候,曾经表达过很有趣的观点,说我们不要重复过往人的做法,我们要有很现代的表达,要创造未来的传统。但法国在我们印象中是很坚持自己传统,很为自己历史骄傲的国家,您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看法呢?
A: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这些文化像是我们背后的一堵墙,推动着我们向前进。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基础,我们才可以在文化的帮助下继续前进,而且它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心。
我相信在传统和新的创造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而新的创造可以说是传统有逻辑的历史性的发展。我刚才也讲到说,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去创新和创造,但这种创造,这种勇气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没有任何责任感的勇气。这种勇气是说我们要能够脱离原来的束缚或根基,去寻找一些新的事情。比如说有朝一日我们会长大,会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去寻找你新的生活。历史不会停下脚步,也不会回头看自己的过去,只会一步一步坚持地走下去。
Q:这几十年中,您对建筑这门学问一直在进行深刻的思考。能否请您谈谈,对比起以往,您感到自己今天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A:到今天这个年纪,我最核心的设计理念没有变,但会感到其中的某些东西,在我心中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而另外一些事情,我却不再在乎了。
比如在年轻时,对于很多具体细节,我会非常较真:这里应不应该挂吊灯,那里是不是得造成透光,等等。今天我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多一点,少一点,不是那么重要了。现在我变得更宽容。其实现在我最大的感觉是,今天的我更自由——我处于这种自由状态之中,不在需要很刻意的去寻觅真理,就会发现,真理往往就在我身边。建筑设计实在是件无比复杂的东西,很难在此简单地把我的思维过程复述出来。不过我可以这样说:现在经过一番寻觅之后,我会更容易到达豁然开朗的状态。那好象是突然的邂逅,我会对自己说:啊,真理就在这里,而且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知道建筑设计实在有太多限制,有太多要求需要满足了。不过这种过程很难解释……
(编辑:映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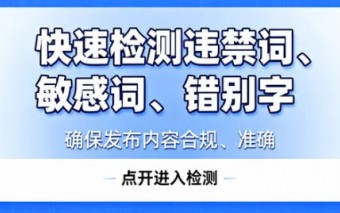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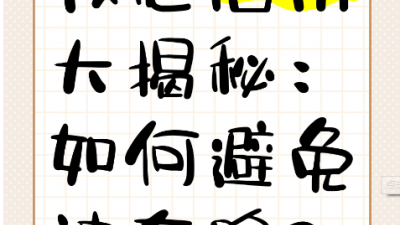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