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女子教育以道德和贞节为主,一般的大家闺秀在《孝经》《女诫》《女训》《列女传》基础上还可阅读《论语》《诗》《礼》《孟子》等。例如司马光在《家范》中说:“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士大夫家一般以家学的形式教授女孩子读书,李清照出身书香世家,她接受的家学是最得天独厚的。李家为经学世家,其父李格非乃北宋文章名流,也愿自己能像蔡邕一样“中郎有女能传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亦说:“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李格非曾任秘书省校对郎,著作佐郎,书房藏书丰富,为李清照接触大量的书籍提供了优渥的外部条件。在宽博自由的家庭教育中,李清照初步形成了独立、自由的性格,拥有一颗玲珑剔透、明辨是非之心。她的笔下既有“轻巧尖新,姿态百出”(王灼《碧鸡漫志》)的长短句,也有老辣犀利、立意高瞻的古诗文,其诗之典赡、词之婉丽获得晁补之的大力褒奖。李清照与喜爱收藏金石刻词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后,情趣相投的两人常常彻夜共赏、展玩在大相国寺“淘”来的碑帖、字画、古玩;屏居青州十年间,在集娱乐和严肃于一体的猜书品茗活动中,博闻强识的她对各类书籍的熟稔度愈发提高。建炎二年赵明诚任江宁知府,据《清波杂志》卷八载“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苦”字内涵丰富,或因李清照的诗句奇巧难和,或是明诚搜肠刮肚只为博得清照一笑。在当时的“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下,李清照那些率性天真的抒情作品的出现,正表明了她所处的学习环境与他人大不同。
李清照 王西京/绘
遍及经史子集的阅读视野不仅使得李清照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也拓展了她的学术视野和人生格局,因而她的诗文,能突破闺阁题材中的缠绵悱恻,对历史、时事有独到的见解。李清照的作品工于用典,出神入化,这与她熟稔史部典籍密切相关,正史的厚重感在她的作品中被消解,“孙寿愁眉”“贵妃醉脸”带有慵懒、感伤的调子,但这并不弱化作品的历史性,历史的深刻与悲壮在以点带面的表述中仍然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意义。她的诗如《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揭示唐朝盛极而衰的根源,以“酒肉堆中不知老”呵斥唐玄宗的骄奢淫逸,穷竭民力而内荒外芜,深刻把握住历史循环往复的规律,托古讽今,寄意深远;文如《打马图序》,开头即以“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立论,继而迭用历史典故加以佐证,虽历数博弈而不繁芜突兀,“议论亦极佳,写得尤历警至可喜”。(清·王士禄于《宫闺氏籍艺文考略》)。李清照在作品中常借古讽今,抒发的感情较之幽怨感伤更加感慨沉雄,其诗《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不仅将项羽刻画为悲剧性的英雄形象,与苟且偷安的赵构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讴歌了项羽以死谢江东父老的可贵气节。李清照从安谧的书斋走向纷扰的现实生活,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葛天氏之民变成“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掊土”(《上枢密韩肖胄诗》)的闾巷嫠妇,这些经历使得她的笔尖不仅凝聚个人的悲欢,也承载着乱世文人的家国情怀。她不仅仅是女作家,更是有着大格局大气魄的一代文人士子的代表,她的作品中蕴含着真挚感人的力量,感动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
李清照对文人别集尤其是李、杜、韩、柳集的偏爱体现了她诗文并重的文学观。她的收藏标准不是藏品的价值而是自己的喜爱程度,赵明诚最珍视的莫过于宗器,甚至要求危急时刻“与身俱存亡”(《金石录后序》)。赵明诚逝世后,她“飘零遂与流人伍”(《上枢密韩肖胄诗》),独自保存大批的善本书画彝鼎,许多书籍在颠沛流离中散为云烟,仅存“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金石录后序》)。这些历尽战火但最终保留在李清照身边的文集、书帖是她回忆与丈夫的点点滴滴的物质载体,是抵抗这乱世人情冷暖的心灵支柱,是李清照个性兴趣的归旨。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她即使在病中也要放在床前把玩,仍“犹复爱惜如护头目”,视这些书不亚于生命。李白、杜甫是盛唐诗代表,韩愈、柳宗元是文章大家,李清照对他们诗文集的喜爱也影响了她的写作风格和成就。李清照的诗、文在宋代为世人所称赞、认可并推崇,朱彧在《萍洲可谈》中称“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首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今作者”;又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赞其“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宋史·李格非传》亦云:“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宋代的卫道士们在传统观念上拒绝承认李清照的过人之处,但从正统的文学观上,却不得不称赞她的诗歌。李清照的作品合集在宋代即已大量结集行世。李清照的诗文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敢于言人所不敢言,她的理想、情操、品格皆融于其中。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中大胆提出“不乞隋珠与和璧”“长乱何须在屡盟”,反对朝廷苟安求盟,远见卓识,真乃女中大丈夫。陶渊明真朴无伪的自然人格也深深影响了李清照的情趣和思想,她于《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受到启发,自号“易安居士”,与丈夫屏居青州期间,将新居取名为“归来堂”,与陶潜一样选择自由与朴真,不愿被社会名利所羁绊。其作文也同陶潜、刘伶般以“真、诚”贯通始终,字字皆真情,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李清照不仅对文人别集感兴趣,她对子部中的一些典籍尤其是《世说新语》特别喜爱,其阅读视野远远超出了闺阁女子所囿的诗文集,具有文人士大夫情怀。其词《念奴娇·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即直接摘引《世说新语·赏誉》篇的句子。李清照熟稔魏晋名士的品行、性情,在作品中有17处引用《世说》中的典故,于典中见喻,典中见论。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谓《世说》:“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一方面,魏晋名士那真率自然、雅量高致、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度潜移默化影响着李清照性情;另一方面《世说》那雅淡韵致,清通简远的文风,滋润了李清照早期的写作风格。李清照的词如“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寥寥十四个字,写尽了三秋桂子的色、香、韵,形神兼备,韵致高雅。
李清照不但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她还是一位思辨的学问家、严谨的文献家。据《金石录后序》记载,她和赵明诚于青州归来堂收藏书画金石,古籍文献有十余间,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卷。自她嫁给醉心于收藏金石刻词的赵明诚后,便一直帮助丈夫收集、考订、整理金石文物,“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二人以学者和鉴赏家的双重身份,对古籍进行修补和校勘,“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初步形成了图书典藏、校勘、版本鉴定、编制藏书目录这样的学术体系。夫妇二人以“正谬误,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的严谨态度,对收集到的书画彝鼎结合存世古籍的记载,通过文献、版本、校勘、辑佚,考订讹误,力求清流溯源,从而厘清了金石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们是最早使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在继承欧阳修《集古录》等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耕耘,成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者。《金石录》的顺利出版,李清照功不可没,她以学者的身份,博古通今,于历史纷纭中拨清层层迷雾,笔削《金石录》,作《金石录后序》,在金石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清照作为“第一才女”,其阅读视野和诗文才情,已经远超同时代的女子,甚至和同时代的男子相比,也毫不逊色,她还走向了严谨的学术研究道路。她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成就,千百年来后人难望其项背,虽未“易安”一生,但敢爱敢恨,洒脱不羁,活出了真实的自我。
作者:仲艳青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编辑:红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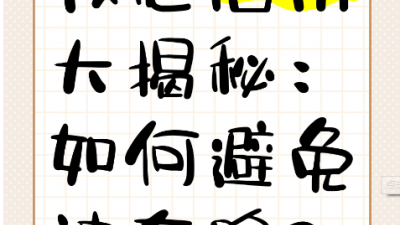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