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曾被进行各种“归类”:青年小说家、人大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员,还有近两年被提及较多的“东北作家群”……这些身份定义了双雪涛在一段时间的身份或者难以抛却的经历的印痕,但却非常难框定他的写作。没有标签代表着不被束缚,可以如双雪涛所述“以无休止的好奇写一切怪怪的东西”,但同时也造成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晰的角度来进行把握,让从小就被训练着“提炼中心思想和把握写作风格”的读者们有些为难。

《平原上的摩西》奠定了双雪涛较为偏好的一个写作题材:凶杀与江湖,《猎人》中的《女儿》《起夜》《武术家》《杨广义》都继续着这一题材,似乎一个远去的江湖、一段尘封的错综的故事能够以时间感延宕出足够丰富的空间让作家去杜撰充满意趣的人物、有悖常理的情节,甚至是完全抛却合理性,写外星人、写影人、写会说话的动物……而即便是相似的题材,也因为切入的角度不同和不时出现的魔幻的意象让这些故事读来充满变化且不知所终。
双雪涛的小说中始终没有那种将一个故事一览无余的快感,阅读时常会感觉到挑战读者经验的叙述的错乱、不合常理的语言的机锋、该严肃和哀伤时猛然冒出来的戏谑、意义不明的情节和戛然而止的结局……借用梁文道的一个评价,双雪涛的小说更像是一个“装置”,作者在其中进行着打破现实框架的实验,而考验的却是与读者的契约关系。
在双雪涛的小说装置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就是他曾谈过的“趣味与想象力”,他说:“我想(在小说中)看见一点超越的东西,也就是小说家核心的东西,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东西,也就是趣味和想象力。趣味不能是恶趣味,而想象力的来源是谦卑的观察,虚心的体会,甚至是从身边的人、亲人、朋友、一面之缘的人,从没谋面的陌生人身上学习,发现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和细节,发现人性在各个境遇里的惊人的表现。”
双雪涛以自己的想象力在小说中构建出魔幻的意象乃至是幻境,就像费里尼的电影里一个在午夜的罗马游荡的作家,在某一个转弯突然就闯入到一个癫狂而神奇的非现实世界,就像《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罗紘武坐着滑索缓缓滑入墨绿色的诡秘的梦境,双雪涛的小说中常有笔锋一转、一个魔幻世界突然降临的时刻:从信封里飞出的带有前世回忆的八哥;穿着一身西装的寻找丢失的一句话的外星人从波光粼粼的湖里缓缓走出来;有形而无质、主人死后化成人形的影人在被念咒语后化作一缕飞烟、被人群的热浪鼓到戏台上;能把人一劈两半的隐于人海的刀客的突然现身……
许多魔幻主义的作品常常是以魔幻来写现实世界的荒诞、本质上要讨论的或许是某段沉重的历史与某种现实;有的魔幻主义的作品则是有意设置魔幻的布景,让故事的主角走过虚假的场景而更能明白生活的真实,如村上春树所说:“我的小说里的魔幻并不像马尔克斯的作品一样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我的小说则更加活生生、更加当代,涉及更多后现代的经验。”双雪涛的魔幻则更加浅尝辄止,似乎并不关于深奥的精神世界和现代性、不关于历史与人类命运,而只是他个人对自己精神领域可以抵达的位置的探求和对于小说这种文体表达空间的拓展。
双雪涛的语言在不断的建立——打破——再建立中形成奇异的跌宕,好像是他生怕某一种情绪过度的驻留,可能刚有一段对话读者读起来觉得悲从中来,接着的马上就是调侃和戏谑,他几乎所有的故事中都没有能贯穿下来的情绪。
而我们也很难讲一个圆融的、自洽的、感情丰沛而一致的故事和一个双雪涛式的错乱的、各种人物和意象进进出出、没有统一的情绪的作品更接近于文学的真实。
读双雪涛的小说,读者也总是需要多走那么一步:即永远不要盲目相信自己一时一刻的感觉和信奉一个故事本就该是情节和逻辑明晰的,有时它可能只是作者的呓语和为无限趋近于小说文本的极限所做的尝试。那么就放弃努力吧,放弃去附会他写的是哪一个人群的苦难命运,放弃去研究他的小说多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经历,一切表达都是值得怀疑的,文字呈现出的本身是一场幻境,最后我们能把握到或许只有某种延宕出的意韵和一些情感上的触动。
之前他尚且在书的前言后记偶尔袒露自己的心绪,谈经历,谈生命,谈死亡,来北京几年后的双雪涛越发少地谈自己,几乎所有采访中他的回复都很简单,最近澎湃新闻也对双雪涛进行了专访。

双雪涛
小说之外,文学之中
澎湃新闻:
这是你的第六本书,这本跟上一本的变化是很大的。《聋哑时代》是比较平实的笔触,带有一点魔幻色彩,后来的作品如《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逐渐变得天马行空,你会有意在写作中调整写作方向吗?或者说是在哪一部作品开始,你发现了一个变更的契机,之后开始发散开来?
双雪涛:
我没有故意调整方向,我写的还是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我认为小说本身具有很多的可能性,在小说里可操作的东西是很多的,这个文体本身也还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虽然小说发展有很长的历史,许多伟大的作家已经创作出了精彩的作品,但是这个题材至今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就在于它内部可开掘的空间,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玩”的人,所以就一路写到了这一本。
澎湃新闻:
你是从公务员中途转向写作,你觉得自己会受到一些写作的体制规约的影响吗?在人大写作班经历了相对系统的培训后,你觉得这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吗?
双雪涛:
关系不是很大。这跟个人的性格有关,而与何时进入写作关系不是很大。我的性格是比较偏向于喜欢各种尝试的。这个写作班主要是一种氛围而不是某种训练,大家在一起聊文学,其实主要不是谈论具体的如何写小说的问题,而是闲聊一些别的问题,营造出一种沉浸在文学中的感觉,是在小说之外,文学之中。
澎湃新闻:
有的小说家会有意远离北上广这种核心的圈子,他们比较依赖特定的环境。于你而言呢?
双雪涛:
是的,每个作家都有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写作和生活是相关的。目前来看,我在北京感觉还是比较平稳的。2015年我选择来到北京就是觉得之前在沈阳有一些压抑,我辞职几年一直在专职写作,需要一些新鲜的东西或新鲜的环境从各个层面去激发自己,如今看来,这个选择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幸运的决定。
有些没有离开家的作家也写得很好,来到北上广的作家也有一些写得不错的,这不能一概而论。就像福克纳一辈子不曾离开他的家乡,而海明威就常常四处走动,但他们都是很好的作家。
澎湃新闻:
东北题材的作品相对有一种凛冽和荒蛮的感觉,比如你之前的作品《北方一片苍茫》,里面有一些这种气息。
双雪涛:
我是比较感谢阅读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在通过阅读进行自我教育,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的精神世界,后者大部分是通过阅读带给我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哪一本书,我不太在意外界所说的风物或是什么,但它确实是我这个小说中需要的,因为它诉说的东西和我想表达的那一代的东西是有关联的。我觉得一些细节,比如江南的作家像是格非老师早年的小说中那种湿漉漉的感觉,这些都是为了内在的部分服务的。格非老师的作品中的引申寓意,后期表达时已经相当利落了。这是一个作家特别好的方面,你可以看到他在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诉说他要表达的东西,随着他的阅历的变化而变化。
标签与契约
澎湃新闻:
比如莫言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但大家还是偏向于用“高密”这样的标签去指认他,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降低作家的区分度和辨识度?
双雪涛:
第一,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太多他人如何辨认我。其次,我不知道莫言怎么看,我觉得外界之前一度给一些作家冠以“先锋作家”的名头,这还是比较简单的概况。“先锋”本身带有一定的试验性,但这些作家随着创作的成熟,慢慢就发生了变化,有了自己的代表作。这本质上还是作家与读者、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有的要面对公众评价的职业其实都会被简化,思考起来比较容易。有一些读者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认识作者,其实每个作家、每个作品都是很不一样的,包括莫言的很多作品,不能说全都是跟“高密”有关系的;还有余华的作品,也不能说每一部都是先锋作品。还有一些国外的作家,比如一提到海明威总会跟“硬汉”联系起来,其实海明威的很多作品都是很细腻的。这些东西都是呆板的印象。
如今,微博、朋友圈每天在生产大量的见解,这些见解如何迅速被人们了解,就是尽量用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你用的方式越是复杂,别人越无法理解。所以在这个时代,简化他人、呆板化他人是比较方便的,也是大家愿意去做的。归根结底就是大家吸收的新鲜知识太多了,需要用一种简化的,标签化的方式记在脑子里。
澎湃新闻:
你会被这套评价体系左右吗? 它会反作用到你身上吗?你是会吸取其中有用的地方还是去反抗它呢?
双雪涛:
我是不太在意这些东西的。如果一个人特别愿意接受这种简单的概括,他阅读出的东西可能就会少一点;而那些愿意去思考的人,他阅读所得的就多一点。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在阅读和吸收其他人的作品时,但凡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也会抑制我的吸收。我习惯把阅读看作一种“信任”,不管你是谁,我都敞开我的怀抱去阅读,去吸收。所以这个评价体系跟读者的关系比较大,而我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吧。
澎湃新闻:
你说的要屏蔽掉先入为主的看法去看一个东西,可是如果是看一个文学作品呢?一部文学作品来到了我们面前,可能本身就带着一些看法,或是因为它的名气而为人所知,这个如何屏蔽掉?
双雪涛:
确实现下情况如此,这就需要你通过自己的角度去看一本书。很多别人介绍的经典作品,我觉得他们看的和我看的并不是一本书。当下有很多书通过营销来到你的面前,它的很多做工其实并没有做好,包括一些西方的译介作品,这些译本中对这本书的概括其实都有问题。还有一些让我意外的书,比如哈罗德·布鲁姆的作品,黄灿然老师翻译过他的《如何读,为什么读》,这个作者当然是非常著名的,但那本书给我一个错误的印象:教人如何阅读的一本书。我本身是不太想让别人指导我怎么阅读的。后来我拿到了一本实体书翻阅了一下,发现它和我想的不一样,原来是对经典作品的深入分析。它完全不是一个通俗读物,反而很艰深。这一方面就是一些营销手段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就是一旦发现一本好书,会有一种乐趣在。
澎湃新闻:
但是当给朋友们推荐书的时候,大家也首先会问“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没办法概括,就很难让人信服。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有待培养,大家太过于依赖中心思想的抓取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双雪涛:
我觉得小说提供的不是知识,现在有很多知识付费的栏目,那些提供的是知识。我个人也做过小说课,在其中我会分享一些小说阅读的经验。但小说本身不是知识,它是一种作品,包含的是审美层面、精神层面、个性层面的很多东西。但是它不能指导人的具体行为,不是行为的种子。就像洗衣机洗衣服一样,它不会针对一两个污渍,而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小说也是这样,它甚至不一定会让你变好,有些很高级的小说极其黑暗,甚至会粉碎你已经建立的世界观。但是仍然有很多的读者愿意阅读小说,我觉得可能是所谓的艺术本身的魅力,不是公用型的,不是有用的,是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我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时刻。我其实不愿意被束缚的很多。但在另一个层面,我是一个比较认真讲故事的人。我有把某种东西传达给别人的热情,但是至于我如何去讲述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层面了。所以我很难讲这是不是我跟我的读者建立的契约,契约本身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对双方的约束吧。但我还是觉得比较灵活一点会好一些。也许读者会更迭变化,旧的读者可能因为后来的预期不符而离开,新的读者也可能会偶然地进来;有些人会觉得你不过尔尔,也有的读者会有“竟然如此”的感觉,这样也是很好的。
澎湃新闻:
之前也采访过一些网络写手,他们的作品相对而言是被读者所要求的。比如书中主人公的一些行为和后续小说的发展走向是由读者决定的。
双雪涛: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契约就很细致了,甚至可以说是和读者的共谋了。是读者参与创作了。一些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考虑,但是这也无可厚非吧。因为每个人写东西都希望得到回报,这都可以理解。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总有一些作者在追求一些其他的事情吧。

《刺杀小说家》剧照,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
情节之外,叙述之中
澎湃新闻:
你的小说里隐含有一种“装置”,构成这种“装置”的有多个部分,比如一些严肃场合的话痨,可以谈谈构成这个小说中的“装置”的部分吗?
双雪涛:
其实是因作品而异的。这种“装置”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比如《女儿》这部作品中就很明显。总体而言,我希望我的小说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里面。这些可能在长篇小说中提的比较多,像是一个复调的多声部的小说;在短篇小说里有时也能尝试一些。我之前写过一个短篇叫《猎人》,讲的是一个人要演一个电影,提到了台词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它是把几个东西揉在一起,产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澎湃新闻:
中国的传统小说,像是《红楼梦》就很讲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可能这是大部人的阅读习惯。但你写了很多,文学中称之为“闲笔”的东西,它可能游离于整个的叙述,但是仍然在这个氛围里,你觉得它承担一些结构性的功能吗?
双雪涛:
其实我应该写更多的所谓的“闲笔”,所谓的叙事上的、结构上的东西其实已经足够多了,把一个故事推动下去不是唯一目标。前面埋下伏笔,后面产生呼应也不是唯一的叙述方法,还有很多讲故事的方法。
澎湃新闻:
你尝试过用小说来呈现电影中的某个画面吗??
双雪涛:
没有。因为电影有它自己的特长,是小说无法比的。比如电影《闪灵》中,尼克·杰克尔森从外面走进来,一边是一个荒芜的酒吧,里面充满了人这样一个镜头。这些东西是电影的东西。
澎湃新闻:
你提到有些东西是顺理成章就流出来的,但有的东西就很难推。你觉得所谓的“难推”和“不难推”如何界定,思考的过程是怎样的?
双雪涛:
它需要调动的东西不一样。这跟处理的题材有关系。比如《心脏》中比较难推的就是情感线,父子关系怎么处理。不是技巧层面的,而是能自然呈现多少内心积压的情感。“苹果”那个主要是时间的游走和跳跃。后者相对轻盈一些。
澎湃新闻:
我之前看到海明威最后的访谈,他曾说自己前一天晚上已经想好了第二天要写什么,第二天醒来几乎就是迫不及待起来完成。你写小说也会这样吗?
双雪涛:
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这是很美好的,但不是每次都有。尽量不要写到精疲力尽再停下来,还是要有一些余富。但每次都有余富其实不太容易。有时候一下就写冒了,也有时候今天没想好,第二天还得继续想。海明威的故事流传很广,包括马尔克斯都深受影响,他说要留点东西以便下次好开始。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了,这一招其实挺有用的,但确实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
澎湃新闻:
之前你说到写短篇小说是因为“杂志上好发”,现在是不是对于写小说有更多的自觉了?
双雪涛:
对,越来越喜欢了。对于我来说,写一个一万字的短篇我是很有激情的。第一,它不会让我写得很疲惫,几天内就能写好初稿,然后慢慢打磨。休息休息然后再拿出来看看。这种节奏我是很舒服的。短篇小说可以有这样的来来回回的过程,浸泡晾干,再浸泡再晾干。另外,我自己也很愿意阅读短篇,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一个,你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这是很有成就感的。最后就是,短篇小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比如一万字内你要表达些什么。它在不断地刺激着我,也一直在牵引着我。
澎湃新闻:
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写小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双雪涛:
重要的是我做出了一个原来世界上并没有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还不丢人。
(编辑;红研)
《科学导报今日文教》征稿可发新闻、政工论坛、学术论文、课题研究、讲座、学生作文、书画、摄影作品、传记、专家、企业专访、广告软文等,欢迎投稿。国内统一刊号:CN37—0016,邮发代号:23—139 电话:010-89456159 微信:15011204522 QQ:1062421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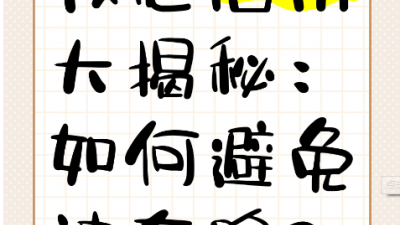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