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一处“剧本杀”门店内,剧本“主持人”在向玩家讲解剧情。视觉中国供图

高碑店导览图。杨杰/摄

高碑店的街道略显冷清。杨杰/摄
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另一种人生,你可以是马戏团的美艳女魔术师,也能变身谍战片里的情报科长,甚至是三国时期的一匹马。在年轻人周围,剧本杀正迅速扩散,全国店面已超过3万家,多过肯德基。
在北京高碑店的仿古建筑里,1公里范围内有二三十家剧本杀店。一家店主指着自家东面的墙,“靠这边能连上这家的WiFi”,又指了指西面的墙,“靠那边能连上那家的WiFi”。
这片北京CBD以东的土地曾以小型文化、传媒公司众多而著称,一排排仿古建筑,俊男靓女穿梭其中,有人笑称,这里谈论的是动辄“不低于一个亿的项目”。现在,这里的热土明显冷却,被另一种“寻找凶手”的氛围浸染,盛产业余“戏精”。
万物皆可剧本杀
剧本杀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在一个故事里有人死了,玩家扮演不同角色,目的是找出真凶。
如何形容年轻人的痴迷呢,在高碑店最早开剧本杀店的王希说,玩家最上头的时候,晚上就睡在布景的道具床上。她的剧本杀店里备有一次性拖鞋、牙膏牙刷和卸妆水。
忠实客户在晚上下班后,背着电脑奔赴而来,在一张大木桌前一边加班,一边等人齐。“一个人在家也无聊,在这躺着仰着,没人管。”有时候人没到,外卖先到了。甚至有剧本杀狂热分子专门搬到附近住。
这里的房子属于高碑店村民。夏日午后,大妈们戴着红箍在伞下聊天,谈论过去车间的故事。男人们在通惠河边安静钓鱼。高碑店是辽金时代的漕运河码头、皇粮商品的集散地,村里旧有娘娘庙、将军庙、龙王庙,现被新修的亭台楼榭取代,像是小型的影视基地。
以前,仿古家具之风吹到这里,建起一条街,至今响着“红木家具,亏本清仓,老板要钱不要货”的喇叭声。后来村民盖起四层小楼,文化、传媒公司相继入驻,“创意”飞满天。
现在,高碑店上空最新鲜的话题属于剧本杀。“陪她看电影,不如陪她演电影。剧本杀是自己无法亲历的故事,年轻人喜欢去体验。”一家剧本杀店的老板龙欣说。她2019年在此开店时,同行不超过3家,现在多了10倍。龙欣同时经营一家传媒公司,跟剧本杀店共享一处空间。玩家的游戏室里有太师椅、白板和纸笔,也是影视开发制作的会议室。
剧本杀是人性的试验场。一场几个小时的局下来,嬉笑怒骂、排斥、争斗、算计、暗战全有了。两个熟人前一秒还在聊着八卦,局一开始,眼睛一翻,立马变脸,猜忌着对方的真实身份。玩家互相搭梯子、互相拆台,上演黑暗丛林法则,争夺决策权。
剧本杀也是一场社交游戏。店主王希出生于1991年,干过家装、调酒、孵化器和媒体,“来北京新认识的朋友都是客人。”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没回家,王希邀请朋友们一起在店里跨年,她洗了一大盆韭菜,大伙围一圈,择韭菜。
有人在店里相识、成为情侣、求婚;有人在剧本前给朋友过生日;有玩家主动帮忙在实景里扮鬼,用冰镇饮料把手冰凉,再“偷袭”客人。
随着剧本杀在年轻人中的流行,大量剧本火急火燎地撒向市场。剧本大多通过展会购买,每个月8场,每场有150个新本,内容与时俱进。比如疫情阶段有《疫不容辞》,还有《赘婿》《王者荣耀》改编的剧本,连《喜羊羊与灰太狼》都能开辟出一场“生死搏杀”。

开个店,年入500万元?
店主王希觉得,大量剧本杀新店是随着一条“开剧本杀店年入500万元”的短视频入局的。
“赚一波快钱。”王希说,有的店家连剧本的类型都没分清就急着开店。一个开过清吧的朋友轻蔑地表示,“这不就是社交。”
仓促组建的剧本杀局状况百出。新手和老手在一起,老手说什么,新手都不相信;有玩家坐着不说话,自己在手机里搜答案;还有人在玩的过程中急眼了,摔本就走;有的情感本,女生哭得一塌糊涂,同局的“菠萝头”(指不容易代入的玩家)丝毫没有波澜。
王希是剧本杀资深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很多是《名侦探柯南》启蒙的。”2018年,她在高碑店开了第一家剧本杀店。隔壁的房子还没装窗户,广场也是一片废墟,外卖店是一片荒芜中唯一亮灯之处。
这两年,她见识了行业的火爆。“你肯定不知道剧本杀的展会什么样!”展会上,没有宽阔的大厅和主题演讲,也没有并排陈列的展台,约200家剧本杀发行公司占据一个个酒店单间,门口竖着易拉宝,门外是人群。
参展的剧本没有精美的印刷和包装,只是一沓A4纸。买家从中午开始,到次日凌晨6点,进入一个个房间抢夺这些纸。深夜一两点,为他们送餐的外卖员还在电梯间排队。有的店家抢不上试玩,只能打听口碑跟风购买。一些限制数量的独家本,店家要在网上拼手速抢货。
王希测算过,开剧本杀店年入500万元,在北京这种城市基本不可能实现。一场剧本杀动辄三四个小时,北京太忙了,租金、人力成本也高。
今年4月,二手交易网站上以剧本杀店“倒闭了”为理由转卖剧本、道具、门店桌椅的数量较前一个月增加了110%。
“现在才开店的人很多不懂这个行业。”王希说,“稍微懂一点,应该知道上游的发行成本低、利润高,更赚钱。”

转型,转型,再转型
秦松是高碑店的编剧,现在兼职剧本杀创作。
疫情前,高碑店南北一纵列,分布着十几家影视传媒广告公司,疫情期间活下来的只剩3家。有的把招牌摘走了,有的没摘。
资本在影视圈砸钱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秦松说他在咖啡馆里谈论剧本,声音有点大,创意就被同行“偷”走了。
当时在行业内,投资者只看创作团队两年内有没有作品,超过两年,“你说过去跟张艺谋拍戏都没用。”两年之内,创作方式、设备、演员价格全部更新一遍。
疫情期间,影视行业受创,线上视频是高碑店少数还能赚钱的出路,网红经济开始在这里冒头。在短视频平台转一圈,偶尔出现仿古建筑一角,它们可能出自高碑店。
疫情之前,高碑店的广告公司就显出颓唐的样子。时代变了,电视广告的转换率很低,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广告的精准投放。
一些广告传媒公司把视线转向剧本杀。有的公司给编剧开设转型的内部课程,还给编剧一笔钱,让他们每月去线下体验。一些无戏可拍的演员当上了剧本杀主持人。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剧本杀写作课程的推广,普通班3000元,直播课上,一半报名的都是学生。
秦松发现,有些专业的演员都没剧本杀玩家演绎得好。一些演员跟空气对戏,有时剧本都没读过,“既没有生命,也融入不了剧情”,全然没有剧本杀玩家投入。
传统影视剧里的男女主角通常是剧本杀里的死者。剧本杀里,每个玩家都可以是主角,其他人是时时在线的配角。“角色自由生长,情节自己形成。”影视剧是单向的,坐在屏幕一侧看另一侧。剧本杀更像VR,360度全息。
秦松提到一个不错的剧本杀,里面有个人物爱占小便宜,恨不得天天找邻居蹭饭,为省几块钱能磨唧20分钟,从邻里到家人都瞧不起他。但这个人物设定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保护他的女儿”——一个小人物的伟大。
一场剧本杀的体验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剧本的质量。秦松说,“有思想的剧本杀少,蜂拥追求利益的时代,大家想的是怎么多卖出一盒。”
年轻人聚会,还能玩什么?
李渊和张媛媛是一对情侣,一个是产品经理,一个是编辑。以往每个周末娱乐的项目是看电视、打游戏,现在,他们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剧本杀。“我男朋友指着开本(玩剧本杀)活着。”张媛媛说,“他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的是,‘不能放弃,那个本还没有开’。”
在体验线下店之前,李渊已经在剧本杀App上玩过100多个本了,他崇尚复杂的逻辑和惊奇的反转。
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李渊想,一帮年轻人的聚会,可选择的娱乐工具有什么呢?
“KTV没有以前流行了,是上一代人玩的,而且如果一个人是麦霸,其他人都得陪着。”密室逃脱只能玩一两个小时,还贵;狼人杀对人数要求高,组局困难。
剧本杀100多元,能玩一下午,“感觉很值”。它对人数的包容性强。“以前十来个人的聚会,总有人沦为配角,或者聚着聚着没事干了,弹尽粮绝,散场又心有不甘。”
“而且剧本杀能吸引来年轻女性这块消费市场,有的喜欢玩情感本,玩完哭唧唧,有的喜欢换装拍照,扮演宋朝的公主。女生来了,不愁攒不来男生。”
张媛媛说自己不像男友一样擅于推理,“思维耐性不是特别好”,但她也能在每一局里发挥作用,比如一些涉及文史知识的小线索,她能给出答案。
年轻男女在剧本杀里感受着新鲜。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剧本杀题材多变,有未知的情节、冲击和CP(情侣)。
“所有的娱乐工具,能调动你的情绪就是成功。”李渊说。
剧本杀是集参与感、恐怖感、剧情、聊天交友、沉浸式色彩于一身的游戏模式。一位玩家说,人对戏剧天然没有抵抗力,更何况是能参与进去的戏剧。
在一次剧本杀局里,李渊体验了扮演人物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回顾过往,“感觉很完满,像一周看完了全部的哈利波特”。
这对情侣在高碑店附近找到了一家钟意的剧本杀店。主持人是配音系毕业的,声音带有沉浸感,他们曾看到主持人“像特级教师备课一样吃透本,写了很多注释,全文背诵”,还看到店家对主持人考试,询问剧本杀里的人物关系和剧情。
李渊和张媛媛相识多年,日常基本不吵架。只有一次,在剧本杀里,李渊扮演的角色要在他爱的张媛媛和爱他的另一个女生中选择,他选了后者。
那是一个情感本,最后复盘的时候,只有张媛媛一个人在哭。李渊觉得“这个哭不单纯”,她还打断了他的发言,“我觉得她贴脸(情绪式发言)了。”
两人回家“意犹未尽”地吵了一架,吵到张媛媛的智齿发炎。下一个周末,他们决定再次扮演新的人生。
(文中王希、秦松为化名)
编辑:映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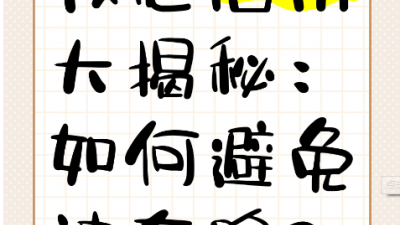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