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资”“妆奁(lián,梳妆用的镜匣)”等。在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一般来说,它在女子出嫁时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家庭贫富,都须尽力筹办。嫁妆的多少常常影响到婚约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可以使女性取得更高身价。在清代,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如助长社会奢靡之风,导致婚后奁产纠纷等。
一、清代嫁妆的种类
在清代,嫁妆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主要是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衣物首饰做嫁妆,可以从最直接的层面体现出新妇之“新”,并且这种“新”不仅要体现在婚礼上,还将一直延续到她结束“新妇”状态为止。
清代学者瞿兑之的《杶(chūn)庐所闻录》中,记载了一位贫妇的嫁妆:“贫人无他长物,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近人徐珂的女仆向他叙述了其弟妇的嫁妆:“布衣三十事,为棉袄、夹袴、棉单、半臂、围裙、裹腿,今有千张皮(碎皮纫成)之袄一,已为绝无仅有。”(《仲可随笔》)这两位妇女嫁妆中衣物首饰较为简单,若富贵人家女儿出嫁,则会陪送大量衣物首饰,数量多的甚至足够穿到去世。
一、清代嫁妆的种类
在清代,嫁妆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主要是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衣物首饰做嫁妆,可以从最直接的层面体现出新妇之“新”,并且这种“新”不仅要体现在婚礼上,还将一直延续到她结束“新妇”状态为止。
清代学者瞿兑之的《杶(chūn)庐所闻录》中,记载了一位贫妇的嫁妆:“贫人无他长物,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近人徐珂的女仆向他叙述了其弟妇的嫁妆:“布衣三十事,为棉袄、夹袴、棉单、半臂、围裙、裹腿,今有千张皮(碎皮纫成)之袄一,已为绝无仅有。”(《仲可随笔》)这两位妇女嫁妆中衣物首饰较为简单,若富贵人家女儿出嫁,则会陪送大量衣物首饰,数量多的甚至足够穿到去世。
衣物首饰之外,女家一般还要陪送被褥、家具等日用器具。在清代的黑龙江地区,男家要事先准备好“被褥各二,及箱柜、梳匣”等日用品,提前送往女家,“俟女家送奁至男家时,携以俱至。女家所增者,尚有洗衣盆、手巾、胰子(肥皂)等物”。(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此即由两家共同预备婚后生活用品,再以嫁妆的形式由女家发往男家。这些婚后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大到箱橱,小到烛台、马桶,与衣物首饰一起组成全副嫁妆。
除了生活用品,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还陪送店铺、土地、宅院等不动产。《清史稿·列女传》记载:桐乡濮氏富而无子,其女的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巨额的嫁妆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如吴三桂之婿王永康,婚前家境败落,漂流无依,婚后则穷极奢侈,俨然厕于缙绅之列。
二、清代嫁妆的规模
嫁妆的多少随女家贫富程度而定,差别很大。清代最为隆重的嫁妆当属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妆奁。如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共二百抬,其实际价值很难估算。此次大婚总共花费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其中皇后的妆奁占不小的比例。
官员家庭的嫁妆也十分可观。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记载一位白姓侍卫“因爱女远离,盛备奁具,媵(yìng,陪嫁)以婢仆百余,雇群艘,由水路行。运奁之日,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者,翌日始毕”。近人吴汝伦的外祖父马鲁迂在蜀地为官,吴汝伦母亲出嫁时“装赀甚盛”。不过由于官员们追求“廉洁”的名声,对女儿嫁妆的实际内容往往比较隐讳,很少见到确切的记载。
与官员的态度相反,商人在陪送时则爱“炫富”。多数商人之女的嫁妆都有银两记载,毫不隐讳,甚至夸大。如有人为昆山学者龚炜之子与某湖商女做媒,特意说明“奁资可得数千金”;又如,山西洪洞人韩承宠娶晋商亢氏女,“奁金累数万”;江宁某商人在义女出嫁时,“奁赠十万金,使成嘉礼”(《清稗类钞》)。
不过,史料中的“千金”“数万”,往往用以形容嫁妆之多,而非具体数额。康熙帝曾恩赏41位因贫困而无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两银子,以筹备嫁妆。乾隆帝亦曾下旨赐宗室贫困者每人“赐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可见,100两银子左右的嫁妆,在清前中期应为一份比较体面的嫁妆。
晚清时嫁妆的数额有所变化。曾国藩一向治家节俭,认为“吾仕宦之家,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礼仪不可太简”。大女儿出嫁时,曾国藩“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为防止讲排场,他一再叮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钱,过于奢侈”。(《曾国藩全集·家书》)从曾国藩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估算,当时200两银子的嫁妆应是既体面又不奢侈。
如果将物价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晚清200两银子的价值与清前期的100两银子差不多。可见,清代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在100两至200两白银之间。一二百两银子的花费,对官僚缙绅和富商大贾而言,根本算不上负担,但贫困之家温饱尚难解决,更谈不上为女儿陪送体面的嫁妆了。许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时出嫁,或找不到合适的配偶。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宗族义庄出资为族中贫困女子置办嫁妆。道光、咸丰年间,常熟邹氏义庄规定:族中贫困之家嫁女给银五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济阳义庄规定嫁女贴钱六千。(《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但这还不是笔者所见的清代嫁妆的最低标准。
清人欧阳玉光妻蔡氏,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这钱蔡氏不忍带走,最后留给老父用以维生。(《清史稿·列女》)三千钱的嫁妆可谓简陋,但根据经济史学者的研究,这对于贫困农民而言,常常相当于一年的家庭总收入,贫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见。
三、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嫁妆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属于消耗品,其价值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而其中的土地、店铺、宅院等不动产,则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后一类嫁妆却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这些不动产不能随着女子的出嫁而迁移。特别是如果缔姻两家相距较远,婚后无论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还是土地和店铺的管理都极为不便。基于此,清代许多家庭在陪嫁不动产时,都会预先考虑到距离问题。清初吴三桂受封平西王,驻云南,而女婿王永康为苏州人,吴三桂“檄江苏巡抚”,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嫁妆;雍正年间,年羹尧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年羹尧在济宁买田19顷,作为女儿的奁田;乾隆年间,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他斥资万两,在附近为其女置买庄田四处。这几个例子说的都是高官显贵,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离遥远,不得不将嫁妆中的土地房屋变卖。
其次,店铺、土地等作为嫁妆,很容易造成经济纠纷。店铺与土地同样不能迁移,但店铺更需要日常的经营与管理。嫁妆中的店铺,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将店铺的所有权、经营权全部转移到女儿女婿手中,改由男方直接经营。如京城崇文门王氏“以质库(当铺)作奁资”,将女儿嫁与一旧家子。婚后夫妻有矛盾,王女骂道:“吾父以数万金之质库舁汝不为薄。”(俞蛟《梦厂杂著》)该质库是以嫁妆的形式全权转赠给女婿,由他直接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二是店铺继续维持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出嫁女只获得收益权。如林则徐的父亲在为儿子们分家时,考虑到已婚的长女、次女、五女嫁妆单薄,决定将龙门口四间店面分给三人,以补从前之不足。
嫁妆中的土地,即奁田问题更为复杂,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奁田属分割产权:所有权在娘家,使用权在夫家。奁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让渡形式,既区别于土地买卖,因为双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又区别于土地的完全转移,因为女家往往对奁田做出种种限制。奁田权属纠缠不清,容易引发经济纠纷,下面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1:道光四年(1824),四川巴县朱太贵起诉姐夫将其姐的奁田随意变卖。朱太贵之姐嫁给赤贫无业的陈以谦为妻,朱家“所赠妆奁服饰不少”,其姐生子陈庆美后,娘家又追赠奁田一份,但规定,田业不准陈家私当私卖,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给陈庆美作为学费,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为陈庆美将来婚娶的费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此案例中,奁田合约明确规定,陈以谦父子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对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严格限制。此合约由“亲族乡戚”作证,即产生了法律效力,陈氏父子不得违背,否则可能导致诉讼。
案例2:雍正六年(1728),刘连俸的祖父将一块土地赠与姑爷张九安以作奁业,当时说明“世守业不问,倘有典卖,业仍还刘姓”。但嘉庆五年(1801),九安夫妇去世之后,九安之子张世文“忘恩负义”,“将业私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这里,女家在陪送嫁妆时亦明确规定:如果男家世代守业,则女家对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过问。然而,一旦男家变卖奁田,女家即要将其收回。也就是说,男家拥有对奁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没有出售权。可见,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对奁田的权利,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使用权和所有权。
作者简介
毛立平,女,1974年生,山西太原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清代社会史、性别史研究。著有《清代嫁妆研究》(独著)《19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合著)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除了生活用品,清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还陪送店铺、土地、宅院等不动产。《清史稿·列女传》记载:桐乡濮氏富而无子,其女的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巨额的嫁妆足以使普通家庭的男子一夜暴富。如吴三桂之婿王永康,婚前家境败落,漂流无依,婚后则穷极奢侈,俨然厕于缙绅之列。
二、清代嫁妆的规模
嫁妆的多少随女家贫富程度而定,差别很大。清代最为隆重的嫁妆当属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妆奁。如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共二百抬,其实际价值很难估算。此次大婚总共花费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其中皇后的妆奁占不小的比例。
官员家庭的嫁妆也十分可观。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记载一位白姓侍卫“因爱女远离,盛备奁具,媵(yìng,陪嫁)以婢仆百余,雇群艘,由水路行。运奁之日,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者,翌日始毕”。近人吴汝伦的外祖父马鲁迂在蜀地为官,吴汝伦母亲出嫁时“装赀甚盛”。不过由于官员们追求“廉洁”的名声,对女儿嫁妆的实际内容往往比较隐讳,很少见到确切的记载。
与官员的态度相反,商人在陪送时则爱“炫富”。多数商人之女的嫁妆都有银两记载,毫不隐讳,甚至夸大。如有人为昆山学者龚炜之子与某湖商女做媒,特意说明“奁资可得数千金”;又如,山西洪洞人韩承宠娶晋商亢氏女,“奁金累数万”;江宁某商人在义女出嫁时,“奁赠十万金,使成嘉礼”(《清稗类钞》)。
不过,史料中的“千金”“数万”,往往用以形容嫁妆之多,而非具体数额。康熙帝曾恩赏41位因贫困而无法出嫁的宗室之女每人100两银子,以筹备嫁妆。乾隆帝亦曾下旨赐宗室贫困者每人“赐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可见,100两银子左右的嫁妆,在清前中期应为一份比较体面的嫁妆。
晚清时嫁妆的数额有所变化。曾国藩一向治家节俭,认为“吾仕宦之家,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礼仪不可太简”。大女儿出嫁时,曾国藩“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为防止讲排场,他一再叮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钱,过于奢侈”。(《曾国藩全集·家书》)从曾国藩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估算,当时200两银子的嫁妆应是既体面又不奢侈。
如果将物价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晚清200两银子的价值与清前期的100两银子差不多。可见,清代中等规模嫁妆的标准,在100两至200两白银之间。一二百两银子的花费,对官僚缙绅和富商大贾而言,根本算不上负担,但贫困之家温饱尚难解决,更谈不上为女儿陪送体面的嫁妆了。许多女子因此不能及时出嫁,或找不到合适的配偶。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宗族义庄出资为族中贫困女子置办嫁妆。道光、咸丰年间,常熟邹氏义庄规定:族中贫困之家嫁女给银五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济阳义庄规定嫁女贴钱六千。(《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但这还不是笔者所见的清代嫁妆的最低标准。
清人欧阳玉光妻蔡氏,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这钱蔡氏不忍带走,最后留给老父用以维生。(《清史稿·列女》)三千钱的嫁妆可谓简陋,但根据经济史学者的研究,这对于贫困农民而言,常常相当于一年的家庭总收入,贫家陪嫁之苦由此可见。
三、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嫁妆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属于消耗品,其价值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而其中的土地、店铺、宅院等不动产,则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后一类嫁妆却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这些不动产不能随着女子的出嫁而迁移。特别是如果缔姻两家相距较远,婚后无论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还是土地和店铺的管理都极为不便。基于此,清代许多家庭在陪嫁不动产时,都会预先考虑到距离问题。清初吴三桂受封平西王,驻云南,而女婿王永康为苏州人,吴三桂“檄江苏巡抚”,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嫁妆;雍正年间,年羹尧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年羹尧在济宁买田19顷,作为女儿的奁田;乾隆年间,于敏中之女嫁入孔府,他斥资万两,在附近为其女置买庄田四处。这几个例子说的都是高官显贵,而有的人家就由于距离遥远,不得不将嫁妆中的土地房屋变卖。
其次,店铺、土地等作为嫁妆,很容易造成经济纠纷。店铺与土地同样不能迁移,但店铺更需要日常的经营与管理。嫁妆中的店铺,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将店铺的所有权、经营权全部转移到女儿女婿手中,改由男方直接经营。如京城崇文门王氏“以质库(当铺)作奁资”,将女儿嫁与一旧家子。婚后夫妻有矛盾,王女骂道:“吾父以数万金之质库舁汝不为薄。”(俞蛟《梦厂杂著》)该质库是以嫁妆的形式全权转赠给女婿,由他直接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二是店铺继续维持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出嫁女只获得收益权。如林则徐的父亲在为儿子们分家时,考虑到已婚的长女、次女、五女嫁妆单薄,决定将龙门口四间店面分给三人,以补从前之不足。
嫁妆中的土地,即奁田问题更为复杂,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奁田属分割产权:所有权在娘家,使用权在夫家。奁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让渡形式,既区别于土地买卖,因为双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又区别于土地的完全转移,因为女家往往对奁田做出种种限制。奁田权属纠缠不清,容易引发经济纠纷,下面举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1:道光四年(1824),四川巴县朱太贵起诉姐夫将其姐的奁田随意变卖。朱太贵之姐嫁给赤贫无业的陈以谦为妻,朱家“所赠妆奁服饰不少”,其姐生子陈庆美后,娘家又追赠奁田一份,但规定,田业不准陈家私当私卖,其每年租谷的一半给陈庆美作为学费,另一半仍存在朱家作为陈庆美将来婚娶的费用。(《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此案例中,奁田合约明确规定,陈以谦父子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对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严格限制。此合约由“亲族乡戚”作证,即产生了法律效力,陈氏父子不得违背,否则可能导致诉讼。
案例2:雍正六年(1728),刘连俸的祖父将一块土地赠与姑爷张九安以作奁业,当时说明“世守业不问,倘有典卖,业仍还刘姓”。但嘉庆五年(1801),九安夫妇去世之后,九安之子张世文“忘恩负义”,“将业私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这里,女家在陪送嫁妆时亦明确规定:如果男家世代守业,则女家对于土地的使用和收益都不予过问。然而,一旦男家变卖奁田,女家即要将其收回。也就是说,男家拥有对奁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没有出售权。可见,清代婚姻中的婆家和娘家各自对奁田的权利,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使用权和所有权。
作者简介
毛立平,女,1974年生,山西太原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清代社会史、性别史研究。著有《清代嫁妆研究》(独著)《19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合著)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编辑:月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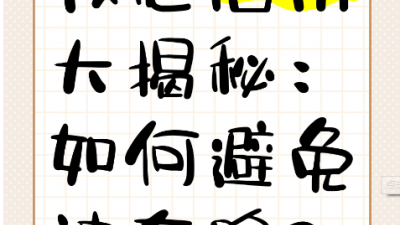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谁在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先用后付”真的香?这些法律风险要注意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7万元注册法国空壳公司 糖果如何变“神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
“高补贴”“高奢品”? 小心仓播里的这些套路